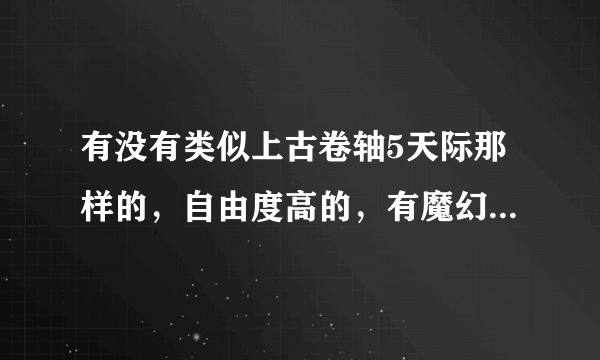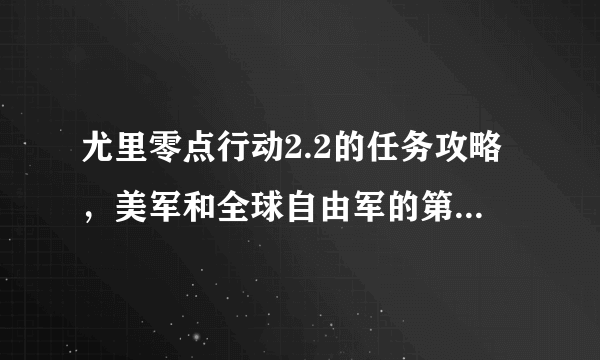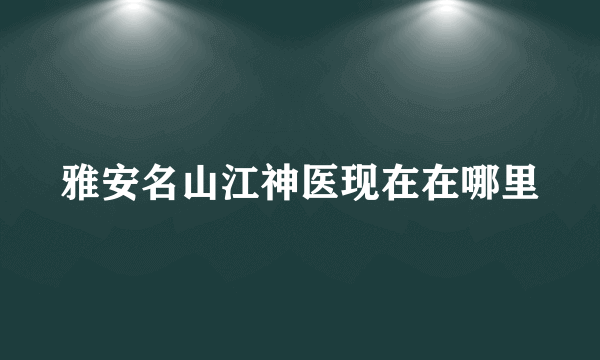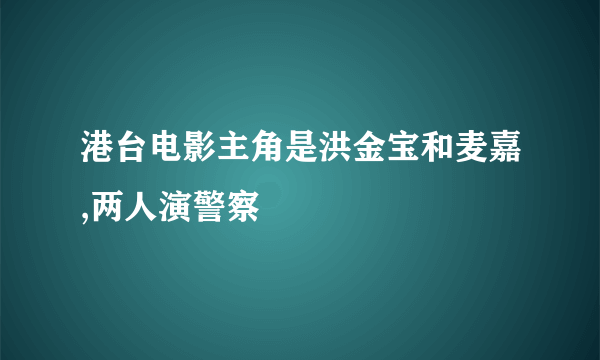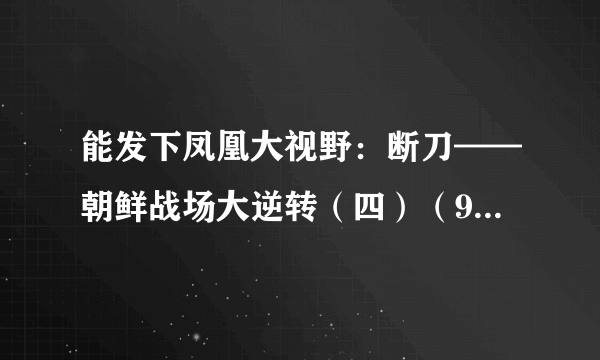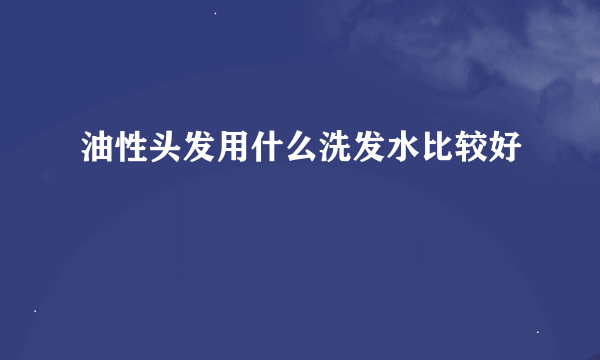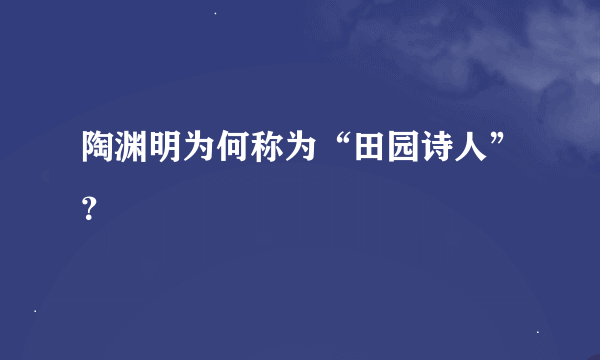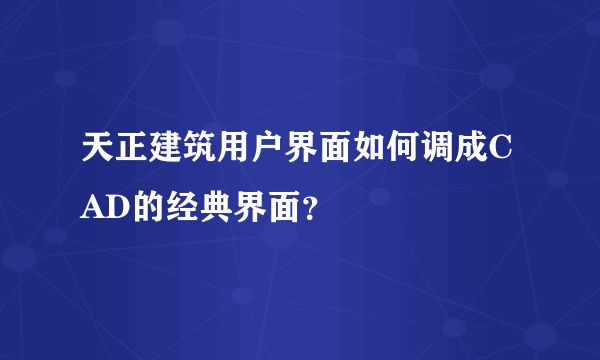容忍与自由的赏析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1959年11月20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做了《容忍与自由》的同题演讲,对毛、殷的批评作了续答与说明。由该文引出的讨论,在当时国民党高压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死水巨波,其影响一直延续至30年后,借用林毓生的话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胡适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论断的?他所提倡的“容忍”,与他所追求的“自由”各自的内涵是什么?这一论断在实践中效果如何?成败的原因何在?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为现实提供参考。 《容忍与自由》一文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政府退至台湾已经数年,当局所鼓吹的“反攻大陆”的迷梦在大多数人心中已经破灭。而台湾当局对外试图给各国一个岛内是“安定中求进步”的自由乐土的印象;对内则采取高压政策,用国民党的伪三民主义压制“五四”以来发展出的各种思想。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下,《自由中国》这本由胡适、雷震等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一定职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以“言论自由”为旗帜的半月刊,发出了难得的另一种声音,甚至成为胡适口中的“中国出版自由的象征”。开始时由于《自由中国》兼具反共色彩,国民党还能忍受,但随着后期反蒋倾向渐渐鲜明终于令国民党大动干戈了。1958年12月,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自由中国》发表题为《欣幸中的疑虑》的文章,暗责蒋介石之任“总统”属于“违宪”,这直接触怒了蒋介石吵判辩。终于1959年3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借口传讯了雷震,所谓“雷震案”就此拉开了序幕。 据《胡氏年谱》载:1959年3月5日下午雷震便来找胡适,胡交给他一封转交《自由中国》编委会的信。信中表示自己早就恳辞发行人的态度,认为“此次陈怀琪的事件(指陈向台北地方法院起诉雷震),我认为我们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3月12日,胡适写定了《容忍与自由》,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做《自由与容忍》,最后改定为《容忍与自由》。此后,在3月24日,胡又对两名《自由中国》的编辑说:“过去的事情还是少说为妙”;在11月20日《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他又作了《容忍与自由》的同题演讲。由此可见《容忍与自由》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对于专制政府的一次上谏。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 其实胡适并非到1959年才提出这一论断的。早在1948年,胡适便多次在演讲中引用布尔教授的话,并提出了“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我们可以注意到那时胡适也面对着自己自由主义阵营里的分化,以罗隆基等为首的左派自由主义者纷纷与国民党决裂转而与共产党合作。而胡适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却与民盟分子们越离越远。胡适与罗隆基等人分歧的根本点就在于对待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上。作为那时北大的校长,前驻美大使,胡适始终持支持政府的立场,无论是面对“李闻血案”,还是“沈崇事件”,他都强调:“国内思想言论自由是局部小事不免,大体说进步了,总之,进步是多,不要性急。”由胡适“容忍”观的发展可见,他所强调的容忍有双重内涵:一是劝政府有容忍的雅量,一是劝他的激进的同道与后学们耐住性子,忍受政府的种种压迫,以换取政府的容忍,而不要采取暴力、激烈的手段。那么,胡适忍了这么久,他所要通过容忍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换句话说,胡适的“自由”概念到底如何来界定? 以塞亚·伯林说:“‘自由’这个字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升缺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冲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全体,而不是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来的原因。……”与“积极自由”相对的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又可称为“防卫的自由”,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最大区别点是:前者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概念,而后者属政治哲学的范畴。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不同追求,以卢梭等为代表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与以洛克、柏克等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法式自由更注重追求积极自由,以建构理性为基础,视所有社会与文化现象为人为设计之产物,强调人们可能通过而且应该通过接受某一原则或计划重组社会结构;而英式自由注重追求消极自由,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相信渐进的改良,相信社会的自发秩序,注重法制下的自由。 胡适作为杜威的弟子,一名实验主义者,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拥有并希望坚持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早期他提倡“好政府主义”,提倡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参加人权运动时,都能始终坚持“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但胡适毕竟是在中国争自由。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由于引入西方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胡适们在理论上不屑于对消极与积极自由作仔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自由只是达到国家富强的手段。这种对自由从工具合理性角度的理解,使胡适们的自由思想中包含有更多的积极自由的观念,胡适始终支持思想文化改革对于中国复兴的意义,所谓“学术上的改革,新科学的提倡,这实在是返老还童最强最有效力的药针”。而在如何进行中国的社会改革这一问题上,胡适毕生宣传实验主义,认为实验主义可以构造出中国的新学术,培养中国人民的新思想,从而达到文化复兴,进而达到国家的强盛。 在争自由的方式上,胡适始终坚持渐进的改良主义,反对一个“根本解决”的存在。渐进的改良,否认“人间天国”本是英式持消极自由观思想家们的思想特色,但当胡适将之运用到中国来后,就又发生了变异。因为英美的渐进道路是要在有一个议会民主制度传统为前提的条件下才能走出来的。而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这条通路是无法通向胡适心中那个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的”。早在1940年,蒋介石就代表保守派说道:“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与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这明显表明了国民党所代表的主导型政治文化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一视同仁,都当做反社会型政治文化加以抵制和斗争。 对于渐进改良的必要前提,胡适并非不知,在1948年名为《自由主义》的演讲中他就指出:“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暴力革命的必要了。”但胡适只看到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看不见蒋先生将他的主义与共产主义早绑在一块儿了。而导致胡适如此短视的原因,便是他坚信实验主义能救中国的积极自由观。他幻想能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下一点一滴地改良,盲目迷信实验主义的威力,才没有听到中国人民的呼声,没有看到蒋氏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这种迷梦并没有因蒋氏政权失尽民心,退守台湾而清醒,相反地仍幻想能通过自由知识分子的容忍来达到国民党的谅解,并采纳他们的意见,从而在台湾建立自由主义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