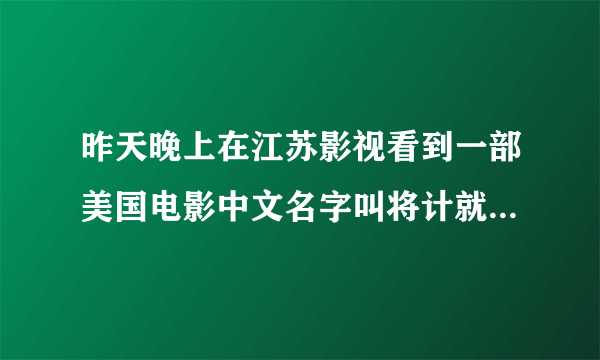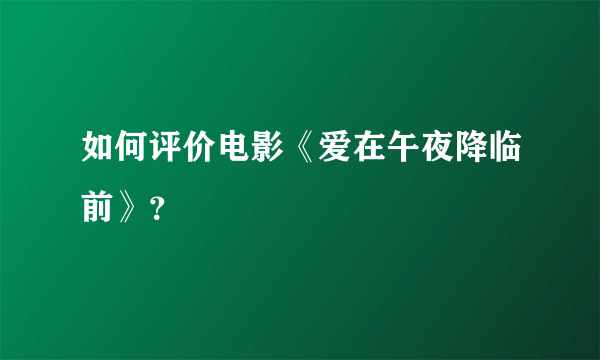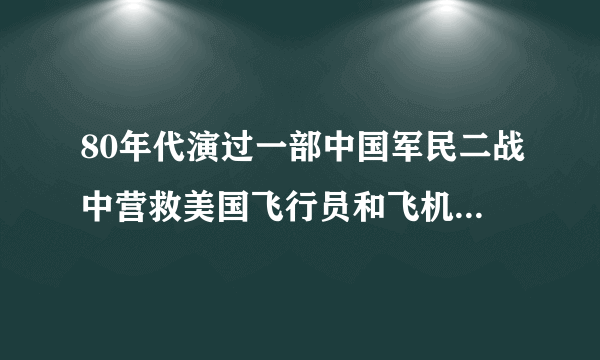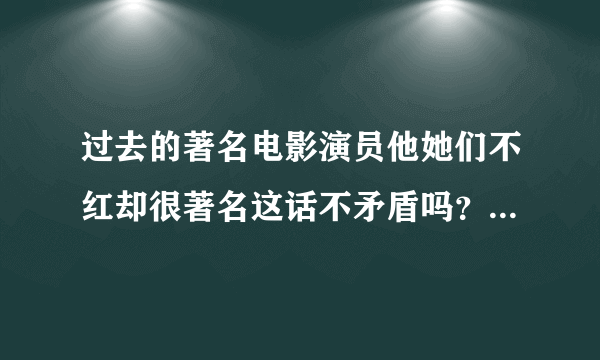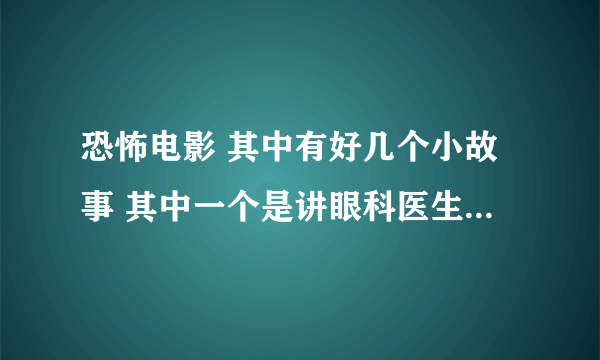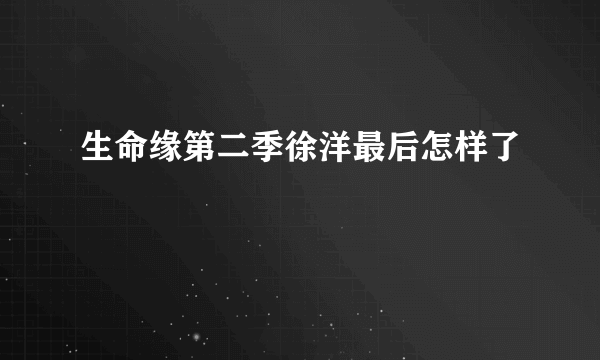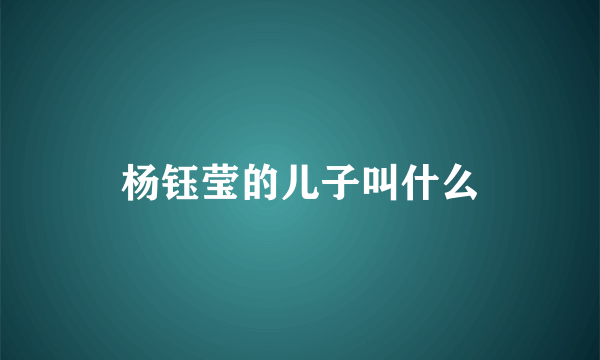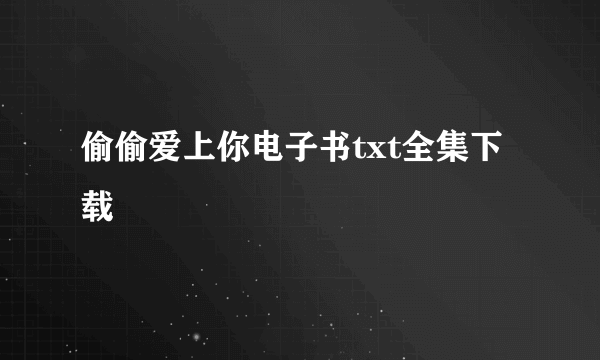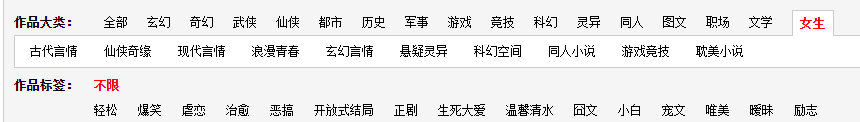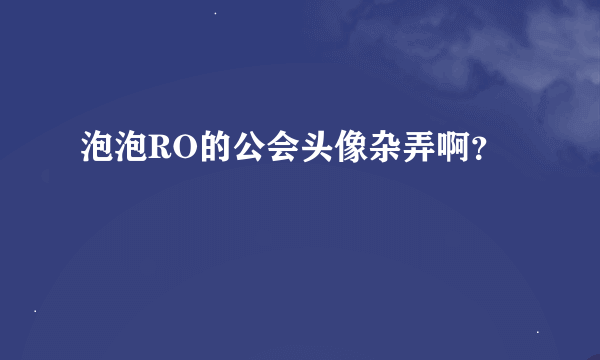电影《立春》影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王彩玲?我得说,我做过一阵王彩玲。 没有憧憬过北京的人,不会知道憧憬北京是什么滋味。 为什么要憧憬北京?因为它是北京。 三年前考研那阵子,我与另外一个女生到教职工居住区合租了个房间住。是一个单元里头带阳台的那间。 那时候人年轻,心里还是有一些郑洞肆隐忍的疯狂,总觉得有点天雷地火的事情即将降临,颤培然而春天一个一个数过去,日子仍是静水无澜。 ——就像王彩玲说的: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那单元另外两间都住的是男生,也都是考研的。其中一个,人瘦削,脸青白,眼睛下面拱出两个颧骨,柳叶形的眼睛常是似笑非笑,似嘲讽又似卑怯。肩背微微佝偻。经常穿灰色的恤。工科生,英语却出奇好,有时比我这个英语专业的人还牛一点——虽然我口头是绝不承认。 ——看到黄四宝,竟觉得神似他的模样。瘦,以及阴郁又深藏焦虑的眼神。居然还有时候有天真神情一闪。文艺青年是不是都一个脸模子?? 一般考研的人一见面都会交流一下考试目标复习进展之类。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他却只是含混几句,一笑,讳莫如深的样子。 之后慢慢知道他在年级里以异类而闻名,是不太合群的人物。 ——在男生堆儿里:每天洗衣服袜子饭盒,不看毛片而爱看贾樟柯,用国家地理图片而不用张柏芝Twins的照片做电脑桌面,每天出去上自习,不熬夜打游戏聊QQ,临睡刷牙,每周购买《南方周末》并做剪报,六级考一次就过而且考到八十分以上....这样大概是够怪异的了。 后来有回下午我自己在屋里写字,临《灵飞经》,他进来了,不出声地看了会儿,拿了我的笔写了几行隶书,居然很有点功夫的样子。他说:我借一本《曹全碑》给你,你来。 就这样混熟了,他才很郑重地说:我是一定要考到北京去的。此话的背景音乐是他的电脑音箱里面放着的《One Night in 北京》。 我说:我也一定要去北京;我要当北京人;虽然北京已经没有它最迷人的城墙了,但是我还是爱它,我要成为那个城市的一部分;我要周末上琉璃厂淘旧书,上国家图书馆看古籍,上北大听讲座,老了退休了早晨到北海遛鸟。 他听完眼睛里面有光,是把我当作自己人了(虽然我说“不听陈绮贞”之后他大叫“敌人!”)。 (他喜欢:贾樟柯、休格兰特、陈绮贞。) 后来我就像王彩玲一样开始止不住地犯贱。如:他饭后喜欢喝杯热茶,我于是每天雷打不动多打一壶开水拎上五楼,贴墙放在他房间门口,专门供他泡茶;晚自习回来,看到壶把不再与墙垂直,就知道他动过了,就满足得心口酸楚一阵。其余送水果买杂志供他看之类,不消提了。 黎巴嫩大牛人纪伯伦说的:“爱情不需要回报,爱在爱里面已经满足了。” 女人是总需要有一个人,让她把她的热情和温柔——甚至狂热——花费出去。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爱,似乎竟是一种生理需求。 有一天终于在他床上拥抱了。 ——大地崩坼,天空翻转,海水倒灌,冰川塌陷,他吻了我。 记得他身子那样瘦,让人很想把他紧紧地搂抱,抱进子宫里去再孕育一回。熄了灯的小屋里,他埋首在我胸口,短头发扎刺着我赤裸的皮肤,像只剩几岁的小童。 ——就像黄四宝又一次醉倒在地上,呻吟一样低声呜呜地哭着,更像是哼着。王彩玲在他身边蹲下。我的心口针扎一样:这样的世间女人共通的怜惜。云雨之后的一夜,王彩玲在镜子前左顾右盼,扎上鲜艳的黄丝巾,微微一笑,光彩流溢。床前留下为熟睡的男人买好的早点。 可是我知道他是不会承认她的。就像我亦始终不曾被承认。 我与他的关系,永远停留在那张床上:下午或晚上,接了他短信,躲过单元里其余两人的目光,溜进他的房间。有时在下床之后、走出房间之前,黯然哭出声来,然他只是似笑非笑地旁观。但第二晚,接到他的短信,我还是会自动走去推他房间的门。 我能给的,只能有这些。再没别的。 几乎想要挫骨扬灰,只为在他心中留痕。 ——甚喊轿至想:这样的委身,这样卑贱的委身毕竟是没有人会做的,他会因为这罕见的卑微而记得我。 那时候,心里有一种狂热的绝望。又因绝望,所以干脆放纵地狂热下去。 他一直一直说,一定要考到北京去。所有人都不看好他。所有人都觉得他无用窝囊不太正常,他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 他把头牢牢揿在我胸口。我抱着他赤裸的身子,心里像是被一块烧热的冰块烫着和冻着。 ——他就是像王彩玲和黄四宝那样的人。人群中是有这样一小撮“一根筋”;他们偏执狂热着一个dream,殒身不恤;但是这种偏执和狂热偏偏有着独特的魅力,对于特定的人来说,这种魅力是致命的。 其实偏执的人,都有格外炽烈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不大常用在人的身上(除非是他们同类)。又大概因为偏执的人目下无尘,觉得人是不配让他们花费感情的。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思特里克兰德待女人的无情和女人对他的飞蛾扑火,庶几相似。) ——后来,他没考上,我的分数差了一点。他选择住到北京继续考,我早早妥协了,调剂到离北京极远地方的学校。 第二年,他的偏执终于有了结果。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他考上了人大,且是高分公费。 《立春》的结尾,所有的人都妥协了。 长头发爱朗诵的周瑜,剪短了头发,生了眼睛倍儿黑的小闺女; 黄四宝也剪了短发,换下了标准文艺青年的行头皮夹克黑长统靴,一边打大哥大一边开面包车; 被领导拿泰国人妖来比的胡金泉老师,踏实坦然地开始坐牢了。 王彩玲虽然还是不结婚,但是总算认真地当起了妈。露出了始终不曾有的笑容。 一切似乎正常了,和谐了,可是却更觉得更凄寒。 (跳芭蕾舞的胡金泉,原本穿着海蓝色大衣系雪白围巾的胡金泉,一身雪白练功衣在音乐中旋转的胡金泉,在监狱之中被剃了光头,竭力想立起穿着黑布鞋的足尖。艺术把他的生命烧成了灰——是不是一定要有人成为艺术的祭坛上带血的牺牲?) 那样狂热的不顾一切的追求似乎可怜;妥协了,又是悲凉。 我说:我还是要再考到北京去的。 我是不是还想在琉璃厂偶遇着他?也许是。那时候,会说什么?.... 也许会说:“看过《立春》没?前几年的电影。那里面有个黄四宝,长得还真有点像你。” 谨以此,纪念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