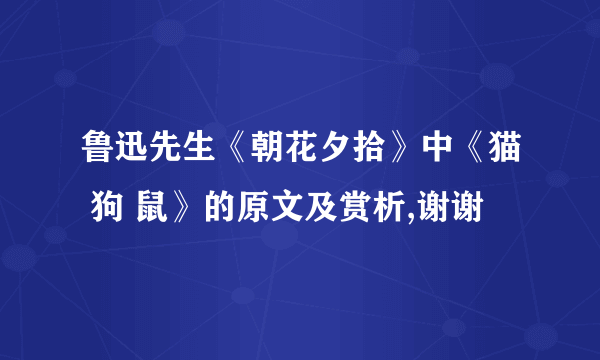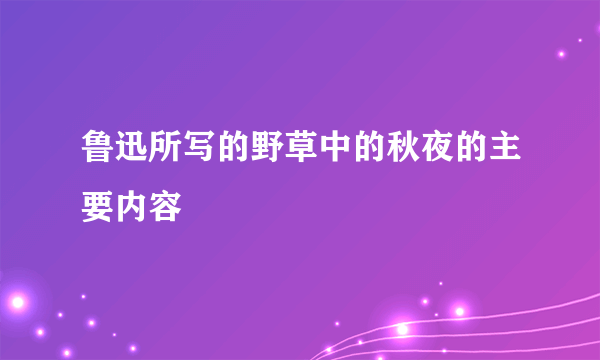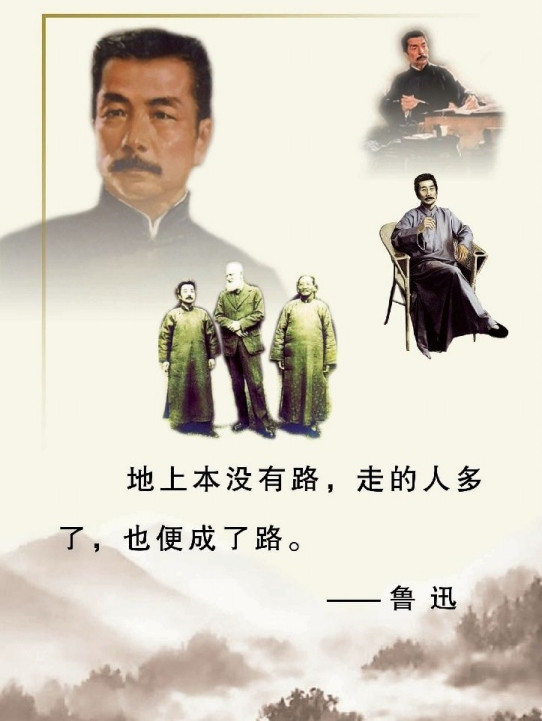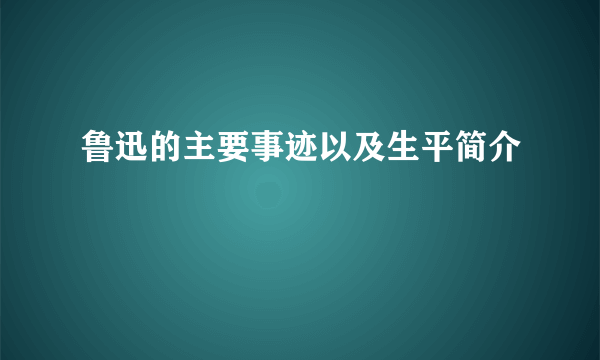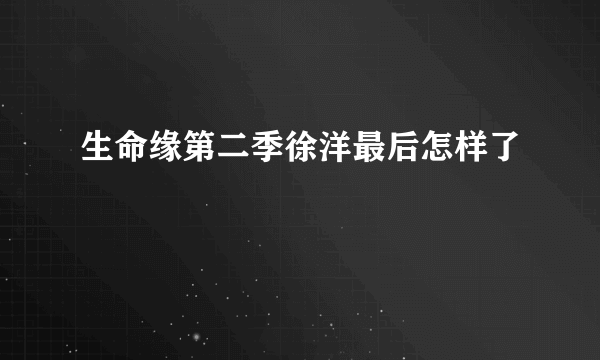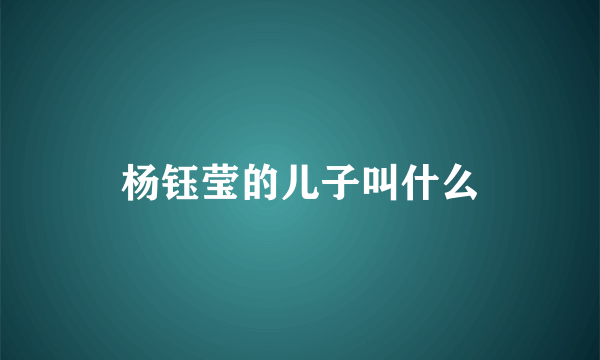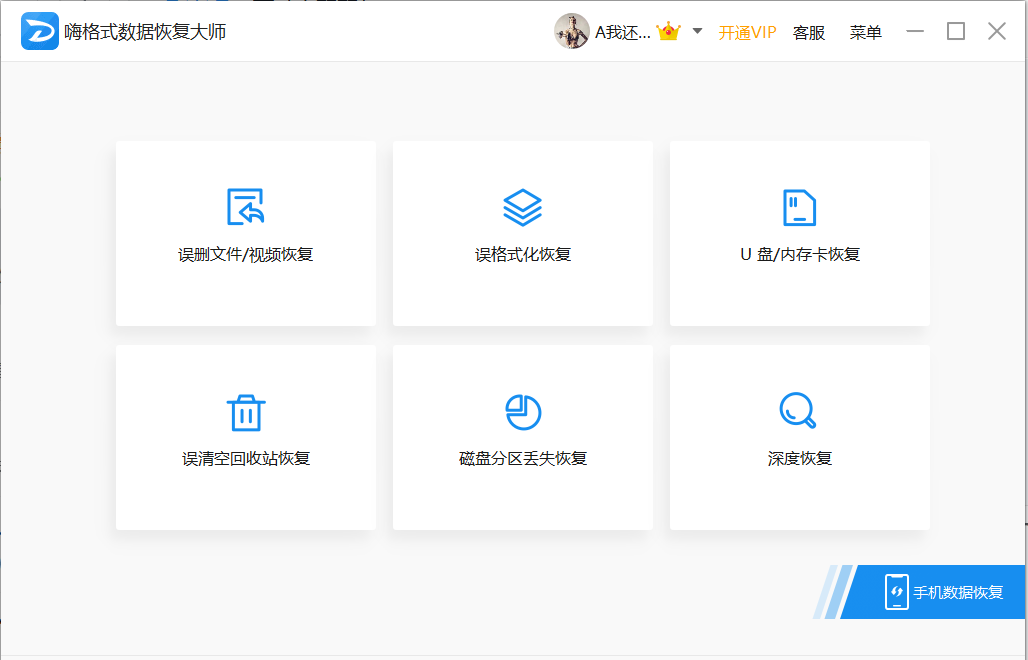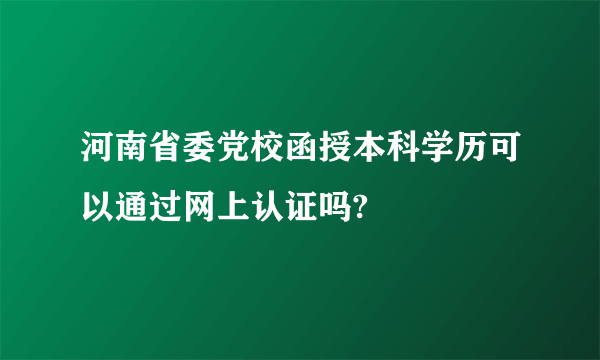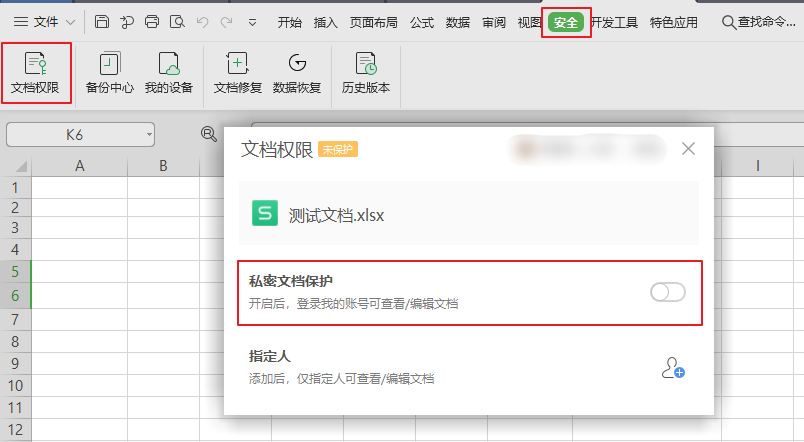《铸剑》中鲁迅为何详写第四部分?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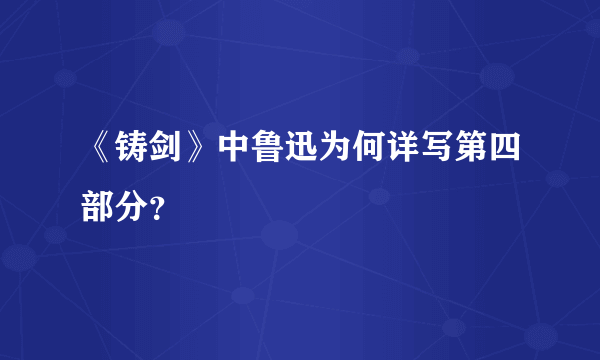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在鲁迅看来“言必有据”的铺排比“随意点染”的敷衍更具难度呢?鲁迅未曾作过正面的解释,倒是他在评论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时所引的一段芥川创作谈,可作一个侧面的参考:“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贴切的合而为一,小说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相较而言,“言必有据”的文本演绎要求自然会对“我”的融入与发挥产生更大的束缚作用。鲁迅自言《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意味着他在严格遵循故事蓝本的同时,巧妙而自然地融入了“我”的元素,使《铸剑》的叙述形态成功地从故事蜕变为小说。 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小说不就是讲故事吗?其实不尽然。据本雅明的辨析,故事旨在传递社群间的经验,给人某种教诲;小说则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对人无以教诲。(《讲故事的人》)在《铸剑》所依据的各类相关古籍(如《列异传》、《搜神记》)中,赤鼻(即《铸剑》中的眉间尺)复仇的叙事完全是情节性的,它试图传达的“教诲”就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广泛遵循的复仇伦理——血债血偿。鲁迅虽然没有改变故事蓝本的基本情节,却以小说家的敏感对故事的主题——复仇——展开了悖论式的探询,呈现出某种不可通约的个体生命体验。 残雪认为,《铸剑》中存在着两种复仇:一种是表面结构的复仇,隶属于亲情道德范畴;一种是本质的复仇,即“人要复仇,惟一的出路是向自身复仇”。(《艺术复仇》)前一种复仇形态也是故事蓝本所呈示的,我们有时把“子报父仇”扩展为“反抗暴政”,其实依然没有走出外在对峙的复仇格局;而后一种复仇转向内在灵魂的撕裂,则是鲁迅“故事新编”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从复仇的主体、对象、动机等方面考察一下《铸剑》中复仇观念的蜕变。 在相关古籍中,复仇主体赤鼻、客和复仇对象楚王的形象几乎是符号化的,只有几个简练的动作来表征他们的身份。复仇双方的界限泾渭分明。《铸剑》则赋予了复仇者与被复仇者丰富的心理内涵,并呈现出相互纠结的复杂局面。像他的原型赤鼻一样,眉间尺一出生就被镶嵌在复仇的框架内,他的生命意义乃至个体生命本身都被复仇精神所覆盖了。但鲁迅并未就此止步,他接着就在被复仇外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眉间尺身上开出了一道心理口子:爱怜、同情与优柔。《铸剑》一开首所展示的眉间尺与老鼠的争斗实际上就是眉间尺跟人相斗的预演,由此暴露出来的心理“弱点”暗示着眉间尺复仇的不可实现性。尽管在行动上眉间尺的复仇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他与王的对峙实际上已相应地内化为眉间尺自身灵魂的分裂。母亲把父亲的仇透露出来之后,眉间尺决定改变自己优柔的性情,用雄剑去为父亲报仇,但他又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不时听到母亲失望的长叹声。天亮后,眉间尺在人群中等着王的来临,正想往前走的时候,一个突然跑过来的孩子差点碰着他背上高悔的剑尖,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人们为一瞻龙颜挤得密密层层,眉间尺又怕雄剑伤人,总是宛转退陪碧避。王的出现虽也使眉间尺全身一冷,继而燃起了灼热的复仇火焰,但他只向前走了五六步,就被人捏住了一只脚,跌了个倒栽葱,然后又被一个无赖纠缠,弄得怒不得,笑不得。可以说,眉间尺在被复仇之“恶”步步导引的同时,始终受着优柔之“善”的牵掣,两者势均力敌,此消彼长,把眉间尺逼到了爱与仇持久对峙的墙角。 复仇也就此陷入了僵局。为了使故事情节得以延续,复仇内涵获得深化,鲁迅接着就安排了一个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出场,也就是《铸剑》故事蓝本中的“客”。关于这个场面,《列异传》是这样叙述的:“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搜神记》的叙述稍详:“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仇。’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以今人的眼光看,这两种叙事都有让人莫名其妙的地方。客与赤鼻素不相识,也跟王无仇,更无利益可谋,却挺身而出要替赤鼻复仇,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戚乱正赤鼻不惜砍下自己的头,把为父报仇的重任托付给一个陌生人,他信托的依据何在呢?故事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如要追究,可能得用古代侠士世界无条件的“义”来解释了。《铸剑》的叙事则正面提出了宴之敖者替人复仇的动机问题。先是眉间尺的猜测——仗义抑或同情,宴之敖者严冷地否定了,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被玷污了,成了“放鬼债的资本”,他“只不过要给你报仇”。复仇本身成为复仇的动机,等于说宴之敖者的复仇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动机,复仇是独立自足的。郜元宝先生就此指出,鲁迅这样设计宴之敖者的复仇逻辑旨在强调“二人朴素的、不能为任何‘名’所范围所定义的单纯的复仇意志”。(《鲁迅六讲》)这种解释固然成立,但因此取消对宴之敖者复仇动机的进一步探询,似有不妥。 当宴之敖者提出要用眉间尺的剑和头去替他复仇时,眉间尺并不像《列异传》和《搜神记》中的客那样干脆、果断,他是既感奇怪,又显狐疑的。宴之敖者劝眉间尺不要疑心,眉间尺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眉间尺依然停留在世俗意义上揣摩着宴之敖者的复仇动机。宴之敖者的回答虽然依旧令人费解,但毕竟比第一次具体多了:“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照语句间的逻辑看,宴之敖者替人复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你我他本是一体的,二是宴之敖者极其憎恶充满了精神创伤的自我。 第一个原因可视作对宴之敖者此前所谓“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的复仇动机的呼应和深化。这里,“你”“我”所指是明确的,“他”据上下文看,当指眉间尺的父亲。宴之敖者在精神层面把自己等同于眉间尺父子,也就是在向世人宣示,“我”宴之敖者替“你”眉间尺复仇就是替自己复仇,谁也不欠谁的,“我”没有让人不得不感激的嫌疑,“你”也不必承担不得不感激的义务。显然,这样的心理内涵已大大超越了“客”的同情或仗义逻辑,烙上了鲁迅式的独特印记。在给赵其文的信中,鲁迅曾多处谈及感激的负面效应,如感激别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过客》里的客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为绝望而反抗,却差点被由小女孩布施所引发的感激之情而裹足不前。既然感激是份负担,那么被感激之人也就有了增加他人负担的嫌疑,而增加他人负担无疑又会让一颗高贵而又敏感的心灵萌生歉疚之情,而歉疚何尝不是另一种负担呢?面对这样的感激困境,鲁迅不得已采取了双向否定的策略:一方面“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另一方面“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求乞者》)似乎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彻底心安理得,才能完全捍卫行动的纯粹性。鲁迅把这种对感激(包括被感激)的高度警惕与排拒的心理内化到宴之敖者身上,无非也是要彻底清除复仇之外的任何牵累,使复仇成为一个坚决、纯粹、自足的动作。而复仇避开了被价值化的命运,也就掏空了它的伦理意义,残雪所谓的“艺术复仇”初显端倪了。 照例,第二个原因也渗透了鲁迅独特的生命体验。大凡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很容易从宴之敖者关于憎恶自己的言辞中听出《孤独者》里魏连殳的声音。先前,魏连殳有信仰,有追求,有操守,虽被视为异端,依然活得尊严而热烈。然而,社会总是属于庸众的,各种流言蜚语终究使魏连殳丢了饭碗,甚至被逼到了求乞的边缘。但是只要有一个愿他活下去的人存在,他就不甘心消亡。等到连这样的人都没有了之后,魏连殳反而解放了,开始给军阀做顾问,赚大钱,获取“新的颂扬”和“新的钻营”。他说:“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这种不得不以扭曲自我精神为代价的复仇行为不正是促成宴之敖者“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的心理动因吗?只不过在《铸剑》里,鲁迅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毒气”与“鬼气”统统抽象成了一种理念化的“恶”,并赋予了一个人身——王。先前,我们可能只关注眉间尺与宴之敖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不大留意眉间尺、宴之敖者与王之间的因缘纠葛。其实,只要撩开复仇的伦理面纱,我们便可发现,眉间尺和王与其说是作为复仇者和被复仇者出现的,不如说是作为人性的正负面而存在的:他们一个优柔,一个暴躁;一个不忍,一个残忍。而这些最基本的对立元素不正构成了一颗真实、博大、复杂的人类灵魂吗?宴之敖者这个人物形象从复仇的表面结构看主要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保证了复仇行动的最终完成。但宴之敖者把憎恶自己视作替眉间尺复仇(刺杀王)的动机,无异于在向世人暗示他与王也是一体的。宴之敖者先用剑取了眉间尺的头,解决了眉间尺面对复仇时的灵魂分裂问题,然后又携着眉间尺的头把剑指向了王,挑起了人类灵魂世界更尖锐、更激烈的战争。《铸剑》第三部分充分渲染了眉间尺、宴之敖者、王三头鼎中相搏的场景,瑰奇神异,高潮迭起,不禁让人感到鲁迅所谓“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墓碣文》)的彻底与决绝。由此可见,宴之敖者这个理念式的人物不仅包蕴着眉间尺与王所承负的人性特征,而且稳稳地高踞其上,在逼视中展示人性的光芒与黑暗,在自戕中领略人生的大痛感与大快感,在复仇与被复仇中尽情荡涤自身盘根错节的矛盾。这样,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就被升华为一场灵魂的厮杀,一段人性的开掘,一次生命的表演,而这恰恰是现代小说所着力关注的。 所以,日本学者丸尾常喜非常重视上述宴之敖者替人复仇的动机问题,认为那段在故事新编时额外加入的复仇动机话语使《铸剑》获得了“思想剧”而非“情节剧”的品质。(《复仇与埋葬》)的确,从复仇的表面结构看,眉间尺、宴之敖者的自杀和王的他杀似乎是一幕同归于尽的传统复仇剧,但是宴之敖者的复仇动机使复仇主体与复仇对象同一化了,这样一来,复仇者在消仇的同时必然要消泯他自己的模式就被纳入到对人性基本矛盾的不懈解决与不断深化之中去了。 然而,当眉间尺和宴之敖者的头确定王的头确已断气,安然地沉入水底之后,复仇并没有结束。很多学者早就注意到《铸剑》第四部分的叙述气氛充满了戏谑、荒诞、滑稽的意味,跟前三部分的庄严、悲壮、诡奇的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钱理群先生把这种文本内部的断裂现象跟鲁迅其他文本中的思维方式(如“娜拉走后”,“死后”,“黄金世界以后”等等)联系起来,提炼出一个鲁迅式的“以后”命题:鲁迅总是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开始“大煞风景”地质疑。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渗透于《铸剑》的复仇观恰恰体现在对“复仇以后”的思考和描写中。当复仇者和被复仇者同归于尽时,王后、王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以及诸多无名的群众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看客集合体,在他们的观看下,复仇的神圣、崇高与诗意顿时消解殆尽。由此,钱先生认为面对看客的复仇必然是失败的,无效的,没有意义的。(《鲁迅作品十五讲》)这样的观点流传极广,有较强的解释力,自然也符合鲁迅对作为戏剧看客的庸众的一贯态度。但细细察之,钱先生未尝没有把诸如《示众》、《复仇》、《药》等文本中的“看与被看”的解读模式硬套于《铸剑》的嫌疑。其实,《铸剑》的主题始终是对“复仇”内涵的不断开掘,而非对“看客”的批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复仇的种子植入眉间尺的生命之后,复仇就呈现出优柔与果决的第一重矛盾;宴之敖者取了眉间尺的头,然后把剑指向了王,使复仇进入了正义与残暴的第二重矛盾;眉宴王三头相搏结束,看客上场,复仇就扩展为眉宴王与看客之间的第三重矛盾,前者将生命力发挥得纯粹而又极致,后者则把眉宴王的搏斗视作可以驱除无聊的表演。三重矛盾逐一递进,复仇的伦理形态渐次消失,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怨恨故事被纯化为一颗灵魂不断接受更高挑战的艺术形态。因此,眉宴王与看客的对峙与其被视作复仇意义的消解,不如理解为鲁迅在开掘复仇内涵时的某种存在性迷失,也就是本雅明所谓的“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从而显示“生命深刻的困惑”。(《讲故事的人》)这样,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就诞生了。